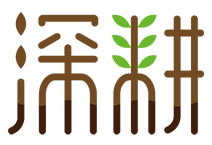在博世中国、广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从化区良口镇长流村委会等多方支持下,华南农村社区发展工作者对话交流会(2021年)于12月20日在从化良口镇长流村举行。交流会由广州市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深耕”)、江西省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江西协作者”)、厦门市春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春野社工”)、湛江市麻章区沃土青年发展服务中心(筹)、通道侗族自治县乡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5家专注于乡村工作的机构联合主办。6位来自不同机构的伙伴分别就农村儿童服务、自组织培育与社区发展、农村生计与生态农业3个主题进行主题分享,并与线下20余位伙伴、线上约170人展开对话交流。
华南农村社区发展工作者对话交流会(2021年)是在2020-2021年的农村社区发展工作者共学计划的基础上举办的。深耕团队自2020年来举办农村社区发展工作者共学计划,与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福建等省份(以下简称“华南区域”)从事农村社区工作的社会组织同行建立了联系。为了凝聚华南区域农村发展领域的伙伴,推动区域内的社会组织发展和伙伴经验共享,协助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乡村振兴,上述几家主办方一起举办了本次对话交流会。
作为共学计划和交流会的支持方,博世中国慈善中心的郑莉惠主任为交流会发来祝福。

交流会落点于“实践者”,风格紧扣“对话”,虽然三个主题略有跨度,但都是农村工作中的真实命题。简单的开场之后,交流会进入正题。
主题一:农村儿童服务
[ 分 享 者 ]
江西省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刘玉方
彝良禾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唐启云

围绕农村儿童服务的主题,来自江西协作者的刘玉方首先以“协作者困境儿童自助图书馆”项目为例,介绍她们在江西农村的实践经验。玉方从江西协作者对农村困境儿童的现状与需求的理解出发,讲述如何以自助图书馆项目来对困境儿童的需求进行综合性的回应。自助图书馆是指在项目支持下,将困境儿童的家庭空间转化为儿童阅读的公共空间,利用简单的硬件设施建立小图书馆,培育困境儿童成为小馆长、自我服务和服务他人,同时也能以工代赈、补贴困境家庭的生计;自助图书馆也能成为社区服务和参与的平台,促进社区互动。
江西协作者目前在江西新余乡村开设有4个困境儿童自助图书馆,共有7个小馆长和11个志愿者,年龄分布小学的中高年级。3年运营下来,团队观察到,困境儿童的能力有明显提升,自信心也增强了很多,家长看到孩子身上的变化也愿意支持孩子管理图书。自助图书馆也链接了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如政府、捐赠人的支持。江西协作者希望未来可以以自助图书馆为基础发展更多的儿童服务空间和社区参与平台,并与政府主导建立的农家书屋结合开展工作,也会进一步深化项目实践。

来自彝良禾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禾心”)的唐启云以“彝良青少年儿童服务实践”为题分享了他返乡5年服务家乡儿童的经验。启云首先为大家详细分享了他对乡村困境儿童现状及其成因的理解(特别是困境儿童在当地的独特状况),归纳出乡村困境儿童在生存、归属和成长三个层面的需求。围绕三个层次需求,彝良禾心希望搭建一个“接得住”乡村困境儿童、又陪伴和协助其成长的网络。在这个过程中,禾心与村两委、民政部门等力量都形成了良好的协作机制,并一直积极动员本地大学生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困境儿童服务中来。
作为一个典型的县域组织,启云和他的团队在这4年的儿童服务实践探索中,也在不断总结和探索,比如如何通过“托管+游学+乡村产品+社会服务”探索服务困境儿童的可持续之路;社会工作者如何从服务者转变为协作者;如何集合本地资源开展社区参与式的乡村儿童服务等等。
在随后的对话交流环节中,线上和线下的伙伴都积极参与讨论,分别就儿童空间的功能、本地村民如何参与困境儿童服务、如何从儿童服务走向村庄发展展开激烈讨论,启云和玉方也分别从自身经验出发谈了他们对这些话题的理解。大家都提到,在乡村做儿童服务,不仅要关注儿童本身,也需要关注乡村本身发展的趋势,“困境”二字并非儿童或家庭本身造成,其背后更有社会结构的原因。因此,社会组织在开展乡村困境儿童服务时,既需要探索成本低、社区/社会广泛参与的服务模式,也需要不断深挖,尝试触碰“困境”背后的社区/社会结构成因。而县域社会组织也与一般的社会组织不同,它会更长久的扎根本地,虽然有资源上的挑战,但其角色并不能简单地放在“介入——撤出”的项目框架里来理解。
主题二: 自组织培育与社区发展
[ 分 享 者 ]
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会/袁玲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何海燕

来自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会(简称“恒申”)的袁玲分享了“姐妹乡伴—乡村妇女自组织支持计划”。作为扎根在福建的基金会,恒申最开始关注的是乡村妇女的个体发展,后来却发现只关注个体无法实现联动,于是从2018年开始启动姐妹乡伴项目。项目以挖掘和培养扎根乡村、有明确目标、致力于解决乡村实际问题的妇女自组织切入点,为她们提供能力建设、跟进陪伴、搭建社群平台、小额活动资金等多元化的支持性服务,以助力乡村妇女实现自我成长与发展、并使其有能力应对并解决她们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袁玲特别带来了前洋村姐妹乡伴团队的案例,讲述该自组织在3年里的意识转变和主体性增强的过程:从“要我做”到“我要做”,人数从5人增至20多人,在内容上从庭院美化开始、到“三留守人群”志愿服务、再到带领村民创业增收。前洋村姐妹乡伴团队成为很多团队想要学习的标杆,一是因为展现了妇女的内生力和主体性,对同辈的妇女群体具有激励、引导和启发的作用,二是作为妇女自组织,她们不仅自我服务,也为村庄带来了改变。袁玲也从内部和外部因素上分析了团队内生力的发展:在内部,妇女自身的思想发生转变,真正把团队的事情内化成为自己的事情,妇女的主体性生发出来;而在外部,村庄给予了支持、信任和机会,团队也很善于对外部资源进行链接、把握和利用。不过,即使3年下来、成果颇丰,作为工作者的袁玲也仍然对自组织培育有不少困惑,比如:自组织内部的核心成员依然比较少,内部更多成员的内在动力应该如何激发?如何保持自组织的独立性、在什么阶段自组织才算独立?所有自组织都需要目标和制度吗?如何保证自组织团队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

来自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简称“山水”)的何海燕也以自身工作的村庄——朝阳村为例,从平衡“保护与发展”、追寻生态公平的角度出发探讨自组织的培育和村庄发展。从2016年开始,山水和朝阳村的互动经过了由浅入深的变化,山水不仅推动朝阳保护中心的筹建,也积极支持保护中心日常巡护监测等工作。2020年开始,山水投入较多资源支持以中蜂为主的社区保护与产业发展。
但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风险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社区保护和村庄发展的正向循环被打破,参与社区保护工作的村民的生计面临风险,保护逐渐成为其“负担”。村民从事社区保护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从“我要保护”转变为“要我保护”,保护责任被固化在保护中心身上。种种压力之下,作为社区自组织的保护中心,也面临内部张力。
保护中心的内部张力促发了海燕及其团队的反思。过去由于依赖单一的社区自组织(保护中心),保护中心好似山水在朝阳村的“代言人”和项目实施方,这种关系可能也影响到朝阳村内部的关系和村民的参与。海燕及其团队调整行动策略,从单一中心走向多主体的融合,实现社区的共同性和凝聚力,在策略上采取组织培育和社区教育的方式,并通过具体事情如本土自然教育课程推动多主体的公共参与,希望最终实现平等互助、公共需求、公平决策、公开商议。
无论是袁玲还是海燕带来的案例,都提到了村庄自组织内部的内生动力、村民的主体性和自组织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也延续到对话中。协作者甘传提到,当我们谈到社区发展、组织培育时,我们讲的到底是谁的发展,这需要我们既要看到伙伴的需求,也不能忽视村民和社区的状况。而作为外部组织的我们也要注重搭建平台,让不同组织形成共识。大家在实践中都会碰到这样的挑战:当村民的主体性出现后,如何让“种子”持续往前走,又如何让TA在面对压力时,创造条件使其意识到身处的复杂关系、发展出相应的行动策略?这样的实践议题,依然需要实践者不断碰撞、累积实践知识才可能有答案。
主题三: 农村生计与生态农业
[ 分 享 者 ]
广西国仁农村扶贫与发展中心/罗立双
深耕/黄亚军

“农村生计与生态农业”主题的讨论,首先由广西国仁农村扶贫与发展中心的伙伴、高级农艺师罗立双的分享开始。他以自身的经历为例,引出了社会组织在协助村民发展生态农业时的挑战和思考。作为高级农艺师,罗立双较早就投身生态农业,自带干粮建立公益组织、给农民普及生态种植的理念和方法,却在2018年发现合作农户的农产品农残超标、与农民合作种植失败、自身生计出现问题后,再次反思生态农业与农村生计、生产和生活之间的关系。罗立双认为,做生态农业就等于选择了不确定性,因为农业需要靠天吃饭,而要求一个普通老百姓像军人一样持续保持高尚情操和自律却是很难的。所以如果要实现生态种植的目标,除了要尊重自然、尊重作物所需要的环境和状态,也需要尊重生产者自身的需求和特性。他对此的总结是“从平衡到平衡”——既需要生产上的平衡,也需要生活上的平衡。
这样的经历让罗立双更加理解小农在做生态农业时面临的困境,因此他也致力于探索如何协助小农在小规模生产中突破、转型为生态农业。他以广西柳州的雷正解从事生态农业的经历为例,呈现小农通过生态种植实现从生计到生活的转变的过程。在这样的实践中,罗立双得出的经验是:“只有把生态生产变成一种有优势的生产力,(生态农业)才更具有生命力”。他认为这是具体体现在生产上、收入上,老百姓所看重的重要一环。
深耕的亚军从“社区为本的农村生计发展”的角度,讲述了深耕的探索。深耕从2007年开始借助CSA的相关理念、探索城乡合作和农村生计发展。十多年来,深耕在农村的探索既包括种米种菜等传统的第一产业,也包括青梅加工等第二产业,更有旅社/民宿/导赏等第三产业的尝试。在城市端,深耕团队开过店、参与过城乡汇、丰年庆的发起和主办。经过这么多尝试,深耕依然死磕农村生计,因此,亚军形容罗立双是“从公益组织的破灭中醒过来”,而深耕“还没醒过来”,在一些问题的探索上越走越深。
这些问题既包括:其一,社会组织在农村生计发展方面,到底是坚守农村的“协作者”角色,还是往前一步、彼此共生?而“协作者”到底是投资源帮村子建起一个产业,还是更应该发展能力?毕竟没有一成不变的外部环境和市场条件。其二,十多年纵向对比、多个村横向对比下来,到底什么样的村子适合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什么样的条件(能力/人)下,村民才能在产业链上承担更多角色?其三,产业发展避不开村庄的能人参与,但与能人合作也有风险,那么,如何转化能人的意识、使其带动更多普通村民参与进来并受益?而最后,回归到社区为本的生计发展这件事上,亚军认为,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生计,显然不能仅以是否赚钱、产业规模等标准来定成败,否则就只是在做一个生意而已;社会组织介入生计背后的价值观/立场和预设,才是更根本的。因此,社会组织介入农村生计,就像上午海燕的分享一样,重点仍在于社区教育和组织工作。
在接下来的对话中,伙伴们继续就商业和公益的区别、不同公益组织介入农村生计的做法和策略、如何提高村民议价空间等议题展开激烈讨论。嘉嵘通过话语表达上的差异,比如在她们的姐妹乡伴项目中往往更多提“创业”而不是“生计”,引出了对“生计”的进一步讨论。林晓风和罗立双都提出,生计其实是生活最基本的需求,是更沉重的;而创业是可做可不做,是自愿的,可以允许失败的,其中不同人群面临的生计状况和所处的背景也就不尽相同。现场还留下很多关于生计的疑惑,如协作者凤连所说,期待接下来还有机会去继续探讨这个议题。
交流会已经结束,但更多可能性正在路上
在三个主题六场主题分享后,甘传也作为主办方代表向更多同行的伙伴发出邀请——作为两年共学营的延续,交流会看似是一次阶段性的经验总结和交流,但主办方其实期待借此机会搭建更坚实的网络,让共同关心农村、扎根农村一线的实践者彼此对话,并实现深层价值上的共识。主办方期待通过更多的共同行动,包括主题共学、联合筹款、人才培养、行动研究共学和网络建设等,为自己、为伙伴带来更多的支持、一起走得更远。

作为本次交流会的支持方之一,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李妙婷也分享了她们的看法并表达了支持。妙婷提到,在农村做发展工作面临的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挑战其实非常多,有些团队可能有7-8人的全职团队,而一些返乡青年成立的机构可能只有1-2人,实际从乡村振兴流动到草根组织的资源是很少的。这也是千禾社区基金会思考搭建平台的动力,千禾依然希望支持扎根一线的团队,让大家更可持续地做事。

疫情之下,由几个草根组织联合主办的华南农村社区发展工作者对话交流会在仓促之中落下帷幕。尽管这次交流会不尽完美,但大家很确定,明年、以及更远的未来,这样的交流会会一直办下去。交流会也会坚持“实践者对话交流”的定位和风格,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伙伴加入进来、共同前行。
··· 联合主办 ···
广州市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江西省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厦门市春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湛江市麻章区沃土青年发展服务中心(筹)
通道侗族自治县乡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 支持方 ···
博世中国
广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 现场对话协作 ···
广州市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甘传、廖凤连、李洁
厦门市春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林晓风
··· 线上直播 ···
湛江市麻章区沃土青年发展服务中心(筹)/何小婷
广州市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阳珍丽
··· 现场记录 ···
江西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袁晶
广州市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田韵、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