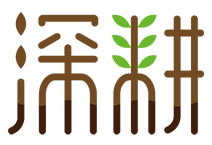深耕大地:青年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2000年,做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总理写信,以湖北江汉平原上的农村为例,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言简意赅。这可能是三农问题首次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大概也是从新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三农”,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以公益人的身份陆续进入农村工作。到今天,TA们前面的远方,只剩下先行者残留的背影;而TA们身边,却有了更加年轻的面孔。于是,在广袤的乡土上,逐渐浮现一些散布在各地的小团队,三两成群、队形各异,也抱着各自不同的想法、走着不同的路线。这些团队,大概构成了公益行业中农村工作的地景。
2013年,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学生阿甘和李洁,也加入了农村工作的行列。绿耕(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作为上述地景中的团队之一,曾凝聚着他们、以及更多的青年。他们在广州市从化区的山区农村,借着发展生态产业、组建农民互助小组和合作社等工作,跟农民建立深厚的关系,也重新理解农村、重新实践自己与农村的关系。
但在农村,青年们深耕、成长,并走到了先行者未曾到达过的地方。在时代背景、三农问题与行业地景的交错中,不同的人有了不同的选择。
随着2004年中央明确提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农村负担大幅减轻、国家对农村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农村在持续面临结构性的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某种意义上的发展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公益行业也更加积极地介入三农问题,在政策的引导/动员下进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各种位置。在多个相关方的要求中,公益人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就更需要公益人长出自己的主体性。
对于像阿甘和李洁那样、最初只是带着模糊的理念进入农村工作的青年们来说,长长短短的农村工作经历,也是TA们长出自己的主体性的过程。TA们从自身经历反思过去以“离开农村”为方向的教育模式,进而也反思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在农村工作中重新认识农村,也尝试建立自己对三农问题和出路的理解;在想着为农民和农村带去一些什么东西的过程中,却发现自己与农民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与此同时,青年们也意识到,要持续回应三农问题,就一定要突破工具化的项目的束缚。
于是,基于自己对三农问题之“为什么、怎么办”的理解,基于现实的社会位置和生存方式,青年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把自己绑在农村工作上、不飘忽,就真的是基层立场、不打折,就和农民一起学着面对、不讲大话。深耕农村,这最初可能只是一个职业选择,而后,成为青年们的生涯选择。
只是,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路应该怎么走?微小的力量,如何面对宏大的三农问题?过去可以跟随他人、无需深思,现在该如何重新思考并落地为行动策略?而被社会和行业结构层层包裹的青年,又该如何安放自身?像阿甘和李洁这样的青年,一头扎进去就是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如何基于农村来想象个人的发展路径?又如何构建一种跟农村工作有关的家庭生活?这些问题,曾经的先行者和理论都给不了答案;单纯靠个人探索,亦难以面对。以团队的方式、踏实行动,才有可能找到一丝光亮。
是在这样的脉络中,一群在三农问题/城乡关系议题上持续探索的资深公益人(也是广义上的青年~),成立了广州市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深耕”)。“深耕”的主创者,就是像阿甘和李洁这样在从化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农村工作者;“深耕”的理事会,则是按照“青年(而非大咖)、资深、身份多元(但理念一致)”等原则组建起来的。大家希望,这些基因能够让“深耕”保住扎根农村的底色,对三农问题提出不同的理解和实践。
未来,“深耕”将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布局中,从一线的社区发展工作和行业支持工作两个层面,积极推动“人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一线的社区工作,直接面向村民,落点于广东,将在各类农村持续探索社区经济/社区互助/社区适应气候变化等议题;行业支持工作,面向在农村的青年工作者,辐射至华南,将和伙伴一起推动农村发展共学营/实践者行动研究/华南农村工作者交流会等内容落地。
“深耕”面世,请多关照,期待同行。

深耕团队2025年1月合照